2014年10月22日22:53 来源:未知 作者:创联室 点击: 次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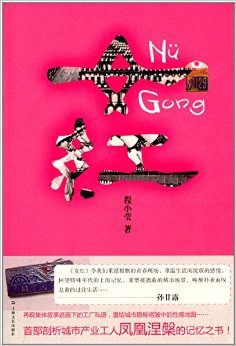
◎李伟长,刊于《新民晚报》
文学有一项功能,就是保存记忆。无论是集体记忆,还是家族记忆,或者是私人记忆,都可以通过文学作品,直接或者间接地得以保存,然后等待后人在阅读中激活。这是我读程小莹长篇小说《女红》,想到的第一条价值。程小莹用文学的方式,保存了一份关于上海工厂,特别是上海纺织女工人的历史记忆。
在程小莹的笔下,呈现出了一个热气腾腾的90年代,一个欲望和迷惘交织的年代,一个纺织工厂开始衰败的年代,一个百万纺织女工开始下岗的年代。作为昔日上海城市的第一支柱产业,上海纺织业造就了一支赫赫有名的产业工人大军,甚至造就了一些“工人贵族”。当纺织业没有了,这支大军也就溃不成军,工人贵族瞬间跌落为社会闲杂人员,这里头的百般滋味,与谁诉说。小说里有个比喻,说纺织业的衰落,就像一只恐龙,轰然倒地,很是悲壮,也实在可怜。即使大如恐龙,说倒也就倒了,说灭也就灭了,称得上是溃败。能够从这份窒息般的困境重新站起来的人,真有劫后余生的感觉。今天再看“下岗”和“再就业”这两个词带着浓厚时代况味的词语,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够体味它所含的屈辱乃至绝望。
《女红》记录下了这段灰暗的纺织历史,在上海文学的轨迹中,这是新鲜的,是独特的,甚至是不可替代的,是我们以前常见的工人小说中不具备的内容。不可能假装这段历史不存在,也不可能漠视这群女工下岗之后各种参差不齐的生活。能够选择写这段城市记忆,《女红》就已经有其价值,能够写得如此温和,甚至带一些悲悯,更为难得。或许只有在时过境迁后,才能平复心境坦然面对过往的伤痛,才会给本来已经足够残酷的生活增加一些温情。
如果说女工题材是一种集体记忆,那程小莹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个人情感更加令人动容。显然,他是有工厂情节的,或者进一步说,像程小莹这样有工厂生活背景的上海爷叔,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地,对已经逝去的工厂生活有着某种眷恋,身体的眷恋,和心理的眷恋。这份眷恋在经历岁月沧桑的过滤之后,越发醇厚,也越发干净,穿透了工厂倒闭下岗的痛苦,甚至对伤痛还有所舒缓和修复,直接回到工厂生活本身。他们的青春年少,他们的爱恨情仇,他们的梦想,甚至他们对女人的渴望与想象,统统与工厂有关,尤其在纺织厂这样女工们扎堆的地方,青春的荷尔蒙一直在发烧,即使在多年以后,不再年轻,再见当年的那些女人,风流依旧漫过心头。
这份单纯的情感记忆,是《女红》传达出的第二层记忆——私人记忆。相比集体记忆,私人记忆更加灵动,犹如无轨的列车、脱缰的野马,任意飞翔,随意穿梭,作者是自由的,是有幸福感的。我们也就完全能够理解,程小莹将当年轰动一时的纺织厂砸锭,工人下岗,写得看似云淡风轻,一点都不残忍,只因为那里有他的青春,有他最好的年华,有他的爱情在。同样还能够理解的是,作者还塑造了一对纺织厂姐妹秦海花、秦海草,姐姐坚守工厂,妹妹早早选择离开。姐姐试图带领工人重新创业的事迹,我更愿意理解为程小莹的工厂情节,他还是不忍心看纺织厂和纺织女工彻底烟消云散,于是赋予了一点崛起的希望。
集体记忆,为的是这座城市,私人记忆,为的是舒缓自己,这两种与纺织女工有关的记忆,彼此交融,也相互冲撞和纠缠,像我这样不曾见过纺织厂风光和纺织女工们发光的人,都会被这本小说迷住,我开始相信,那些有过纺织生活的人们,比如当年的男人们,当年在工厂里捉弄青年男工的女工们,如果能读到这本书,将会怎样泪流满面,甚至放声大哭。这是文学的魅力,更是生活本身的魅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