您当前的位置:主页 > 专题 > 领导致辞 > 2015上海国际文学周
2015年08月21日15:43 来源:东方早报 作者:徐萧 点击: 次
诗人沈苇携《新疆词典》与批评家何言宏共话“去地域化的地域写作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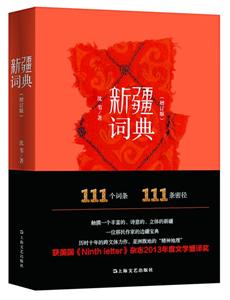
▲ 《新疆词典(增订版)》收录了数十篇沈苇散文作品。

▲ 沈苇(右)与何言宏在周三的书展上。
2015年,诗人沈苇一口气拿了“花地文学”年度诗歌金奖、十月文学奖、第13届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年度诗人奖、首届李白诗歌提名奖等几个重要的文学奖项。批评家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言宏甚至因此在出席近日活动时,将文学上的2015年称作为“沈苇年”,他表示:“在文学史上,经常会因为某个作家、某个作品,形成某种思潮现象,引起整个文学界甚至社会上的高度关注,因此这一年会被称为‘某某年’。今年(2015年)应该可以被称为‘沈苇年’。”
对此沈苇则比较淡然,“什么什么年,更像是媒体的说法。每个年都属于自己,又都不属于自己。”实际上,沈苇成名很早,1998年33岁的他就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,2008年、2011年又分别获得刘丽安诗歌奖和柔刚诗歌奖两个重要的诗歌奖项。沈苇觉得自己今年之所以能引起些关注,主要是时隔20年,他又有诗集在“内地”出版了,引起了评论家的再评价。
这里说的内地,是相对于新疆这样的边疆而言。湖州人沈苇1988年入疆,一待就是27年,比他在江南的时间还长。这样沈苇在身份上,表现出一种双重性,尽管他的诗歌充满了新疆的地域气质,但他一直希望能够摆脱掉地域性的笼罩,进入到一种更为开阔的、只面对“人”的言说。
8月19日,在上海书展“国际文学周”活动“文学对谈:《新疆词典》与新疆表达”上, 沈苇带着他再版的《新疆词典》与何言宏进行对话。活动结束后,沈苇应采访要求将早报记者拉到了朋友安排的晚宴上,这样我们得以观察到一个更加细腻、有性情的沈苇。
23岁,逃往新疆爱上新疆
1988年,刚刚从浙江师范大学毕业一年,年仅23岁的沈苇跑到了新疆,成为一个“闯入者”。
在很多种场合,沈苇对于当初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,都是从宏大的时代背景进行描述:“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青,向往边疆,常常脑子一热,带上简单的行李,怀里揣很少一点钱,坐上绿皮火车就奔新疆、西藏去了。”但是更为直接的原因其实更加私人和简单,初恋失败和对父亲的反抗。他想逃离那段伤心的恋情和父亲的“阴影”,逃得越远越好。
新疆带给年轻的诗人巨大的震撼。这种震撼首先是一种身体感受和反应,从潮湿到干旱,身体变得敏感了。“人到一个新地方,只有身体爱上了这个地方,心灵才能逐渐认可。”沈苇说,当时很多人和他一样,“盲流”进疆,但是很多人吃不惯羊肉、面食,很多人受不了干旱的气候,最终都离开了,“我不是这样,我的身体一下就接受了新疆并且爱上了它。”
从“地域分裂症”到“去地域化的地域写作”
童年和青年时代对一个人的影响,无疑是巨大和深远的,沈苇也是,他不可能忘掉他的江南身份。而在新疆生活了27年,沈苇的思想和视野成熟于此,这让他的身上又带有明显的“新疆特质”。所以他曾说他得了“地域分裂症”,一半属于江南,一半属于新疆。“江南觉得你是新疆的,新疆又说我是外来的,我就这样被踢来踢去。”在饭桌上,沈苇感慨道。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“悬空的人”。
如何让这两种身份和谐共处,沈苇在《新疆词典》中写了一则《青蛙移民》,以寓言的形式说出他的努力:一只南方青蛙凌空一跃,进入到中亚腹地。为了在干燥环境下与林蛙、蚁狮、戈壁蝉交友,它首先要蒸发掉一部分水汽。但要生存,还要“从空气和石头里采集水分”,来保持蛙皮的湿度。
显然,沈苇就是那只南方青蛙。“既要散掉身上多余的水汽,同时又从新疆沙漠里汲取保持湿度的资源。”在他的诗歌里也是,新疆和江南都是关键词,他提出以“综合抒情”、“混血之诗”这样的方式来消弭身份上的焦虑。这让沈苇觉得,他和张承志、昌耀这样的边疆作家、诗人有点不同,“我给新疆注入了一点潮湿。”
尽管被踢来踢去,但沈苇显然从新疆和江南那里获得足够多的养分。尤其是新疆,我们从《新疆词典》《新疆盛宴》《鄯善 鄯善》《新疆诗篇》《喀什噶尔》等作品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。
沈苇称,地域性只是一个立足点,不应该成为写作者的囚笼。他希望通过地域性这个口径,来揭示下面的普遍人性。
活动现场,一个读者问他应该如何使自己的旅行变得有意义,沈苇说,“多和当地人聊聊”。这是经验之谈。在进入新疆后,沈苇做了12年的记者,这让他经常能够深入到那些“定居者”和“旅行者”所看不到的角落。在写自助旅行手册《新疆盛宴》时,半年时间里,他跑了南北疆,胶卷拍了150卷,本子记了将近20个。
进入到中年之后,他又花了不少时间阅读了新疆的史籍、神话、史诗、古典诗歌、民间文学等。这让他对新疆的过去和现在、虚构和现实,以及当地人的生死和爱欲有了深入的理解。活动现场,他随口就能来上几句维吾尔或哈萨克民歌。
在早期的诗歌创作中,沈苇努力使自己的两个地域性身份达成和解,但随着理解的深入,他发现无论是新疆还是江南,都是一种叙述上的虚构。
地域不是只有景物,构成它们的更主要是人。“我生活的地方,不管是汉族、维吾尔族,还是其他少数民族,都是人在那里生活。”这让沈苇后期的诗歌,开始表现为一种“去地域化的地域写作”。就像在《沙漠,一个感悟》(2003年)这首诗中写道,“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”,以此提醒自己不要成为地域的“寄生者”。
少数民族文学只露出冰山一角
中国的西部边疆从来就不缺乏描述者,西藏的马丽华、魏志远,青海的昌耀,内蒙古和回疆的张承志,新疆的周涛、杨德益,还有沈苇。
西部边疆通过他们,在文学上进入我们的视野。然而“被代言”的新疆是不是新疆,“被代言的西藏”是不是西藏?
起码不能说是全部,隐藏在他们背后的是庞大而失语的西部本土文学。或许,在某种程度上,昌耀、沈苇他们这种汉语作者对西部边疆的讲述,对当地文学多少造成了遮蔽,但根本上,遮蔽它们的原因,更加复杂、更加巨大。
“少数民族的母语文学就像是沉在水面下面的巨大冰山,而露出来只是一角。这一角就是以汉语来写作的。”不过现在,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开始使用双语写作,这使得一部分人进入到以汉语为主要或唯一写作语言的内地文学界。当然,在沈苇看来,使得更多以母语写作的作家和作品发出声音,才是我们今后不断要思考的。沈苇这几年,特别注意对当地母语写作者的推介。过几天回新疆,他就有一个研讨会要组织,是为了一个哈萨克族作家而开的。